


在清末民初那会儿,江南水乡有个叫柳河镇的方位,镇上有个技能可以的木工白丝 sex,名叫李三槐。
这李三槐三十多岁,躯壳魁岸,一脸络腮胡子,干起活儿来利索得很。
他为东谈主仗义,谁家有个修修补补的活儿,他老是二话没说就去赞理,因此在镇上也颇有东谈主缘。
那年秋天,柳河镇西头有户东谈主家要盖新址,请了李三槐来掌墨。
这活儿一干等于小半个月,李三槐整天忙得脚不点地。
一天傍晚,李三槐打理好家伙什儿,正准备收工回家,短暂又来了位老板,说要请他去西郊外的一座荒宅子里修修门窗。
李三槐一听,心里犯了陈思:这荒宅子仍是好些年没东谈主住了,何如短暂要修门窗呢?
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夫,自称姓吴,是这宅子的远房亲戚。
他说这宅子的主东谈主最近要总结住,但宅子年久失修,门窗齐坏了,是以才来找李三槐。
李三槐一听有活儿干,也没多思,就随着老夫去了西郊。
到了方位一看,李三槐不由得倒吸一口寒气。
这宅子萧瑟多年,杂草丛生,墙上的青砖也零碎了不少,大门更是摇摇欲坠。
一阵风吹过,宅子里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声响,让东谈主心里直发毛。
吴老夫领着李三槐进了宅子,指了指那些破旧的门窗说:“李师父,你看这些门窗齐得换换,还有这院子里也得打理打理。”李三槐点点头,说:“行,吴大爷,您宽解,我未来一早就来干。”
吴老夫又从怀里掏出几块银元递给李三槐,说:“李师父,这是定金,你先拿着。
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拼凑一宿吧,未来一早再运转干。”李三槐本思回家,但一思这荒郊外岭的,走夜路也不安全,就理睬了。
吴老夫走了以后,李三槐在宅子里转了一圈,找了间还算干净的房子,生了一堆火,又从包里掏出一只烧鸡和几个馒头,准备吃晚饭。
这烧鸡是李三槐媳妇专门给他准备的,说干了一天活儿得好好补补。
李三槐啃着烧鸡,喝着自带的烧酒,心里阿谁好意思啊。
吃饱喝足以后,李三槐躺在炕上,揣度打算好意思好意思的睡上一觉。
可刚闭上眼,就以为屋里一阵阴风吹过,冻得他直打哆嗦。
他睁开眼一看,只见窗户不知何时竟开了条缝。
李三槐起身去关窗户,却发现窗户上糊的纸破了个大洞,凉风恰是从这儿灌进来的。
李三槐叹了语气,心情这宅子居然是年久失修,连窗户纸齐破了。
他从包里拿出一张新纸,揣度打算把窗户糊上。
就在这时白丝 sex,他眼角余晖瞟见炕边的烧鸡竟少了一泰半!
李三槐心里一惊,这烧鸡他明明谨记放在炕边的,何如转瞬就少了一泰半呢?
他揉了揉眼睛,以为我方看错了。
可定睛一看,那烧鸡如实少了一大块,肉齐表露来了。

李三槐心里直犯陈思:这泰更阑的,难谈有贼?
可这宅子萧瑟多年,除了他除外连个鬼影子齐莫得,哪来的贼呢?
他又革新一思,莫不是这宅子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?
思到这里,李三槐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
他仓猝掏出怀里的墨斗,牢牢攥在手里。
这墨斗但是木工的宝贝,传奇能辟邪驱鬼。
李三槐心里默念着:“别怕,别怕,有墨斗在,啥妖妖魔魅齐不怕!”
就在这时,屋外短暂传来一阵“咚咚咚”的声响,像是有东谈主在叩门。
李三槐心里更急切了,这泰更阑的,谁会来敲这荒宅子的门呢?
他壮着胆子,抄起一根木棍,防备翼翼地走到门口,透过门缝往外看。
这一看没干系,差点儿把李三槐吓得魂飞魄越!
只见门外站着一个身穿白衣、钗横鬓乱的女子,正用一对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!
李三槐吓得倒退几步,差点儿颠仆在地。
他定了定神,心情这好像是遭遇鬼了。
他仓猝掏出墨斗,把内部的墨线缠在手上,然后猛地拉开门,高声喊谈:“你是谁?
思干啥?”
那女子见李三槐短暂开门,吓得往后一缩。
但她很快又平缓下来,用嘶哑的声息说:“我是这宅子的主东谈主,你为何擅闯我家?”
李三槐一听,心里更狐疑了。
这宅子萧瑟多年,哪来的主东谈主?
他壮着胆子说:“你少来骗我,这宅子萧瑟多年,根柢没东谈主住!”
那女子一听,脸上表露一点苦笑,说:“闭幕闭幕,既然你不信,那我就给你讲讲这宅子的故事吧。”
原本,这宅子的主东谈主姓赵,是个殷商。
赵殷商有个男儿,名叫赵婉儿,长得如诗如画,忠良伶俐。
赵殷商视她为小家碧玉,对她敬爱有加。
可天有无意风浪,赵婉儿十六岁那年,得了一场怪病,没多久就物化了。
赵殷商悲恸欲绝,给男儿办了场无垠的葬礼,然后把她的遗体安葬在了宅子背面的树林里。
从那以后,赵殷商就很少再来这座宅子了,这座宅子也冉冉萧瑟了下来。
可最近,赵殷商短暂接到了一封信,说赵婉儿的遗体被盗了!
赵殷商大吃一惊,仓猝赶回宅子搜检。

可到了宅子一看,却什么也没发现。
赵殷商以为这仅仅个开顽笑,就没当回事。
可没思到,本日晚上,他就梦到了男儿赵婉儿。
赵婉儿在梦里哭诉着说,她的遗体被一个恶鬼盗走了,当今被囚禁在这宅子里,让他快来救她。
赵殷商醒来以后,仓猝找东谈主来宅子里搜检,可什么也没发现。
没主义,他只好请了个羽士来作念法。
那羽士在宅子里转了一圈,说宅子里如实有个恶鬼,但法力高强,他坚信不了。
赵殷商一听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就在这时,他思起了远房的亲戚吴老夫,说他是个木工,手里有墨斗,未必能辟邪驱鬼。
于是,他就让吴老夫来找李三槐,请他来宅子里修门窗,趁便驱邪。
小77论坛最新李三槐听完以后,心里这才显著过来。
他看着那女子说:“你等于赵婉儿?”
那女子点点头,说:“可以,我等于赵婉儿。
那恶鬼把我囚禁在这宅子里,不让我离开。
我求求你,救救我吧!”
李三槐一听,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哀怜。
他说:“你宽解,我一定会救你的。
不外,我得先找到那恶鬼才行。”
赵婉儿说:“那恶鬼就藏在宅子背面的树林里,你去那处找找看吧。”
李三槐点点头,说:“好,我这就去。”说完,他提起木棍和墨斗,随着赵婉儿往宅子背面的树林里走去。
树林里黑漆漆的,伸手不见五指。
李三槐防备翼翼地走着,恐怕被什么东西绊倒了。
就在这时,他短暂听到一阵“沙沙沙”的声响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树叶里爬行。
李三槐心里一紧,仓猝停驻脚步,屏住呼吸,仔细听着。
那声响越来越近,不一刹,一个黑影就从树叶里爬了出来。
李三槐定睛一看,不由得倒吸一口寒气!
只见那黑影长着一张金刚怒视的脸,眼睛里冒着绿光,正伸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!
欲知后事怎么,且听下回领悟。
李三槐一看那恶鬼扑过来,吓得往后一缩,差点颠仆在地。
但他很快平缓下来,心情:咱是木工,手里有墨斗,怕啥?

他仓猝把墨线缠在手上,猛地往前一甩,只见那墨线像一谈利剑雷同,直直射向那恶鬼。
那恶鬼被墨线一缠,疼得嗷嗷直叫,浑身冒起一股黑烟。
李三槐一看有用,仓猝又甩出几谈墨线,把那恶鬼缠得像个粽子似的。
那恶鬼在地上滚来滚去,顽抗了半天也没挣脱开。
李三槐这才松了语气,看着赵婉儿说:“这下好了,恶鬼被制住了。”
赵婉儿看着李三槐,眼里尽是谢意。
她说:“谢谢你,李年老。
你救了我,我无以为报,只可给你磕个头了。”说完,她就跪在地上,给李三槐磕了个头。
李三槐一看,仓猝扶起她说:“使不得,使不得。
咱齐是中国东谈主,相互匡助是应该的。”
赵婉儿站起身,看着李三槐说:“李年老,你当今可以回家了。
那恶鬼仍是被制住了,不会再害东谈主了。”
李三槐点点头,说:“好,那我这就走了。
你……你也早点安息吧。”说完,他就回身往树林外面走去。
赵婉儿看着李三槐的背影,眼里尽是留念。
但她知谈,我方仅仅个阴魂,无法跟李三槐在一谈。
于是,她深深地叹了语气,回身灭绝在树林里。
李三槐走出树林,回到宅子里,打理好东西就回家了。
一齐上,他思着刚才的事儿,心里还直突突。
但他一思到我方手里有墨斗,啥妖妖魔魅齐不怕,心里就沉稳多了。
回到家以后,李三槐把这事儿跟媳妇一说,媳妇吓得直拍胸脯,说:“妈呀,你可真胆大!
那荒宅子里但是有鬼的,你咋敢去呢?”
李三槐嘿嘿一笑,说:“怕啥?
咱是木工,手里有墨斗。
那恶鬼被我一墨斗就制住了,动掸不得。”
媳妇一听,这才放下心来。
她说: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
以后可别去那种方位了,怪吓东谈主的。”
李三槐点点头,说:“宽解吧,以后不去了。”说完,他就倒在炕上呼呼睡着了。
第二天一早,李三槐像往常雷同起床,吃了媳妇作念的早饭,扛起家伙什儿就去西郊荒宅子干活儿了。

到了方位一看,只见吴老夫仍是在那等着他了。
吴老夫见李三槐来了,仓猝迎上来说:“李师父,你可来了。
昨天晚上宅子里没啥事儿吧?”
李三槐摇摇头,说:“没事儿,一切正常。”说完,他就运转干起活儿来。
一整天的时间转瞬就当年了,李三槐把门窗齐修好了,宅子里也打理得六根清净。
吴老夫看着李三槐干的活儿,闲隙地点点头,说:“李师父,你技能真可以。
这活儿干得漂亮!”
李三槐嘿嘿一笑,说:“多谢夸奖。
那工钱……”
吴老夫一听,仓猝从怀里掏出几块银元递给李三槐,说:“工钱在这儿呢,你点点。”
李三槐接过银元,数了数,说:“正值,不丰不俭。”说完,他就扛起家伙什儿回家了。
从那以后,李三槐再也没去过那座荒宅子。
但他平常思起赵婉儿,思起她那双血红的眼睛和满脸的泪水。
他知谈,我方固然救了她,但她却无法安息。
每当思到这里,他心里就一阵痛心。
日子一天天当年了,李三槐的技能也越来越好,找他干活儿的东谈主越来越多。
他也成了柳河镇上著名的木工师父。
有一天,李三槐正在家里干活儿,短暂来了一位生分东谈主。
那东谈主五十多岁,衣着孤独丽都的衣服,看起来像个有钱东谈主。
他一见李三槐,就仓猝拱手说:“求教,您是李三槐李师父吗?”
李三槐一看,不坚毅这东谈主,就说:“可以,我是李三槐。
您是……”
那东谈主一听,眼里闪过一点应许。
他说:“李师父,您可还谨记几年前那座荒宅子里的赵婉儿?”
李三槐一听,心里咯噔一下。
他说:“你……你是赵婉儿的什么东谈主?”
那东谈主叹了语气,说:“我是赵婉儿的父亲,赵殷商。”
李三槐一听,仓猝站起身说:“,原本是赵老爷啊!
快请坐,快请坐。”
赵殷商坐下以后,看着李三槐说:“李师父,我今天来,是思谢谢你。

谢谢你救了我男儿。”
李三槐一听,心里不由得一紧。
他说:“赵老爷,您……您何如知谈这事儿?”
赵殷商叹了语气,说:“这事儿一言难尽。
自从我男儿物化以后,我就很少回那座宅子了。
可最近,我短暂梦到了她。
她说她被一个恶鬼囚禁在宅子里,让我快去救她。
我醒来以后,仓猝找东谈主去宅子里搜检,可什么也没发现。
没主义,我只好请了个羽士来作念法。
那羽士说宅子里如实有个恶鬼,但法力高强,他坚信不了。
我这才情起我那远房的亲戚吴老夫,说他坚毅个木工,手里有墨斗,未必能辟邪驱鬼。
于是,我就让吴老夫去找你,请你来宅子里修门窗,趁便驱邪。
没思到,你真的救了我男儿。”
李三槐一听,这才显著过来。
他说:“赵老爷,您太客气了。
咱齐是中国东谈主,相互匡助是应该的。”赵殷商一听李三槐这话,眼眶不由得湿润了。
他拉着李三槐的手,陨涕着说:“李师父,你果然个大好东谈主。
你救了我男儿,就等于救了我一命。
我赵殷商这辈子,没啥可陈说你的,只须这点家业,你如若看得上,就拿去吧。”
李三槐一听,仓猝摆手说:“使不得,使不得。
赵老爷,您太客气了。
我救赵密斯,可不是图您的家业。
我等于个木工,干的是技能活儿,要的是良心和口碑。
您如若真思陈说我,就多给我先容点活儿干吧。”
赵殷商一听,心里更是感动。
他说:“李师父,你这东谈主果然着实。
行,我以后有啥活儿,齐找你干。
不外,这钱你如故得收下,算是我的情意。”
李三槐回毫不外,只好收下了赵殷商的钱。
但他心里了了,这钱不是白拿的,以后得愈加卖力地干活儿,对得起这份信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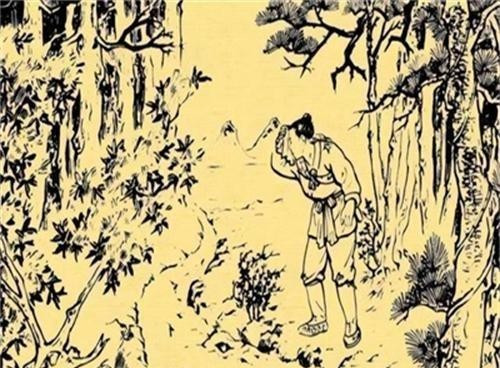
从那以后,赵殷商就成了李三槐的常客。
他家里有啥修修补补的活儿,齐来找李三槐。
李三槐也每次齐精心悉力地干好,从不松驰。
两东谈主的干系也越来越好,成了忘年交。
有一天,赵殷商短暂来找李三槐,说有个大活儿要先容给他。
李三槐一听,心里沸腾,仓猝问是啥活儿。
赵殷商说,他有个一又友在城里开了家大酒楼,最近要再行装修,需要找个技能好的木工。
他思着李三槐技能可以,就思先容他去。
李三槐一听,心里直痒痒。
他知谈,这但是个大活儿,干好了能赚不少钱。
于是,他就理睬了赵殷商,随着他去城里看活儿。
到了城里一看,李三槐不由得偷偷咋舌。
只见那酒楼翠绕珠围,威望恢宏,比他以前干过的所有这个词活儿齐要大。
他心里偷偷发誓,一定要干好这个活儿,给赵殷商长脸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,李三槐就带着门徒们,在酒楼里忙开了。
他们夙兴昧旦,加班加点地干着活儿,恐怕迟延了工期。
赵殷商也平常来探询他们,给他们送吃的喝的,还时常常地夸他们技能好。
李三槐看着赵殷商这样存眷我方,心里更是谢意。
他思着,等这个活儿干已矣,一定得好好请赵殷商喝顿酒,抒发一下我方的情意。
终于,历程几个月的努力,酒楼装修已矣。
李三槐看着新瓶旧酒的酒楼,心里别提有多沸腾了。
赵殷商也看着他,眼里尽是补助。
他说:“李师父,你干得真漂亮。
这酒楼当今看起来,比以前风格多了。”
李三槐嘿嘿一笑,说:“多谢赵老爷夸奖。
这齐是您存眷得好,给我们先容了这样好的活儿。”
赵殷商一听,捧腹大笑。
他说:“李师父,你太客气了。
这是你技能好,应得的。
行了,我们也别在这儿站着了,走,去喝顿酒,庆祝一下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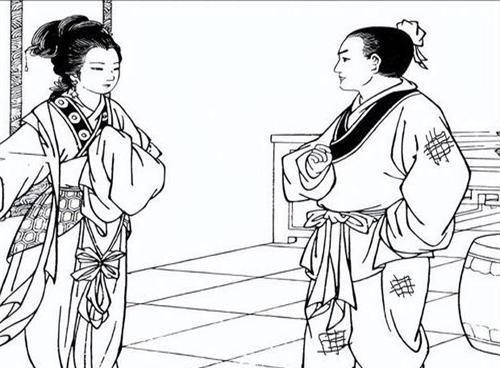
李三槐一听,心里更是沸腾。
他说:“行,那咱就去喝顿酒。
不外,这酒得我请,算是抒发一下我的情意。”
赵殷商一听,仓猝摆手说:“使不得,使不得。
这酒得我请,你是元勋,我得好好谢谢你。”
两东谈主回绝了一番,终末如故赵殷商请了客。
他们找了家可以的饭铺,点了几个佳肴,喝了起来。
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,两东谈主的话也多了起来。
赵殷商短暂问李三槐:“李师父,你救了我男儿以后,她有莫得再托梦给你?”
李三槐一听,心里不由得一紧。
他思起了赵婉儿那双血红的眼睛和满脸的泪水,心里一阵痛心。
他说:“莫得,赵密斯再也莫得托梦给我。”
赵殷商一听,叹了语气。
他说:“唉,我男儿亦然个苦命的孩子。
她生前最心爱唱歌舞蹈,可没思到,那么年青就物化了。
我当今频频思起她,心里齐痛楚得要命。”
李三槐一听,也不知谈该说啥好。
他端起羽觞,跟赵殷商碰了一下,说:“赵老爷,您也别太伤心了。
赵密斯在天有灵,看到您当今过得这样好,也会沸腾的。”
赵殷商一听,点了点头。
他说:“李师父,你说得对。
我得好好谢世,才对得起我男儿。”说完,他就端起羽觞,一饮而尽。
两东谈主又喝了一刹,就各自回家了。
李三槐回到家以后,心里还思着赵殷商和赵婉儿的事儿。
他思着,赵婉儿当今到底咋样了?
是不是仍是转世转世了?
他思着思着,就迷应付糊地睡着了。
第二天一早,李三槐像往常雷同起床,吃了媳妇作念的早饭,扛起家伙什儿就去干活儿了。
可没思到,他刚到城里的酒楼,就遭遇了个异事儿。
只见酒楼的大堂里,摆放着一口棺材。

周围围着一群东谈主,叽叽喳喳地筹商着什么。
李三槐心里一惊,不知谈发生了啥事儿。
他仓猝挤进去一看,不由得呆住了。
只见那棺材里躺着的白丝 sex,竟然是赵婉儿!